金基德的粉絲,和他的電影一樣,多數都存在於網盤裏。
為什麼突然提到這個韓國自己都不願意承認的電影導演?
是因為新舊交替,總想推薦一點回顧視角的電影。所以腦子裏自然地就冒出了他的電影《春夏秋冬又一春》。
金基德早期電影的原始、暴力、生猛,獲獎無數,也備受爭議。
作為中期的作品,2003年的《春夏秋冬又一春/春夏秋冬(港) / 春去春又來(臺) 》,則更加的成熟,用更內斂的手法講述了一個深沉的故事。
並非所有輪迴都指向喜悅,它也可能關乎成長、罪孽、修行與頓悟。
丨 春夏秋冬又一春/春夏秋冬(港) / 春去春又來(臺)

電影講的,其實是我們耳熟能詳但又沒有深究過的故事——
從前有座山,山裏有座廟,廟裏有兩個和尚,老和尚對小和尚說,從前有座山......

湖心孤島寺廟,遺世獨立,四季交替輪迴,這裏只有一老一少兩個僧人。

春,天真燦爛,生機盎然。
小和尚在河邊玩耍,正用繩子把石頭綁在小動物身上,看著他們費力撲騰,負重爬行。
小和尚咯咯笑著,眼裏沒有善與惡,只有好奇與無知,好奇這些生靈的結局。


師父將這一切盡收眼底,他搖搖頭不發一言,只默默找了一塊更大的石頭,綁在熟睡的小和尚身上,讓他感同身受。
無知之惡,亦是惡。
你所施加於他人的,終將以某種方式回到你自己身上。

夏,熱烈和悸動,清淨的廟宇關不住勃發的激情。
多年後一個美麗的女孩來到寺廟養病,小和尚血氣方剛情慾萌動。
師父只是輕嘆:“淫慾喚醒了佔有的慾望,這會導致殺身之禍。”


慾望本身不是罪,但緊隨慾望而來的佔有、執著與失落,纔是痛苦的根源。門外的世界,遠比他想象的廣闊和複雜。
但他已無心參透,心中只有美人,眼裏再無佛陀,他選擇義無反顧地踏入紅塵。

秋,再次回到寺廟,已是多年以後。
他衣衫襤褸,與塵世眾人已無分別,只是身上多了一重嫉妒殺妻的罪孽,殺人的刀,還殘留血跡,他跪在師父和佛祖前想要以死謝罪。

師父不語,只讓他做一件事,用這把殺人的刀在庭前刻下般若心經,審視自己的罪孽,雕刻渡己的經文。
警察幫他把經文塗上顏料,靜待這場儀式完成,然後將他帶走,他先於法律一步完成了自我審判。


小船劃出幾米,便靜止不動,他轉過身,對上師父深深凝望的眼神,這是他們之間最後的道別。

冬,萬物沉寂,湖水冰封。
金基德所飾演的徒弟服刑完畢,回到了空無一人的廟裏。師父已選擇圓寂。
他從湖底撈起師父的舍利,放置於親手雕刻的冰佛眉心。在冬日的晨光中,他鑿冰取水,禮佛修行。



一個蒙面女人抱著一個嬰兒前來,又在深夜溜走,卻不幸掉進了冰窟,和尚收留了這名棄嬰。

無心之惡,亦是惡。
他赤裸著上身,將拉石磨的粗繩盤在腰間,將石佛捧在胸前,一步步負重前行。
他喘息,跌倒,再爬起,親自丈量罪孽的重量,直到筋疲力盡,直到與那份重量合而爲一,他在度人,也在度己。



這部電影,有一種俯瞰眾生的悲憫。
山門守著無形的法度,裡面是修行與剋制,外面是慾望與紅塵。小和尚犯戒、沉淪、返璞歸真,都是人性必然的軌跡。

2011年4月,金基德把自己關進冰天雪地的小屋裏,裹著被子看著《春夏秋冬又一春》畫面中的自己,大哭不已。
他想到了什麼而哭?答案不得而知。
這一切都被他放進了個人紀錄片《阿里郎》。

那時他還沉浸在《悲夢/夢蝶(臺) / 非夢》女主演李娜英拍攝事故的驚恐裡。
因為一場獄中自縊的戲份,他希望儘可能真實,所以遲遲沒有叫停,導致一線女演員差點窒息而死。
這場事故引起了軒然大波,韓國媒體對其口誅筆伐,民眾群情激憤。於是他躲進了山裏,避世三年,蓬頭垢面,日復一日,像他電影裡那些底層的邊緣人,活得孤獨、清醒且痛苦。
他複述著人們對自己的謾罵,也不斷拷問內心所謂的追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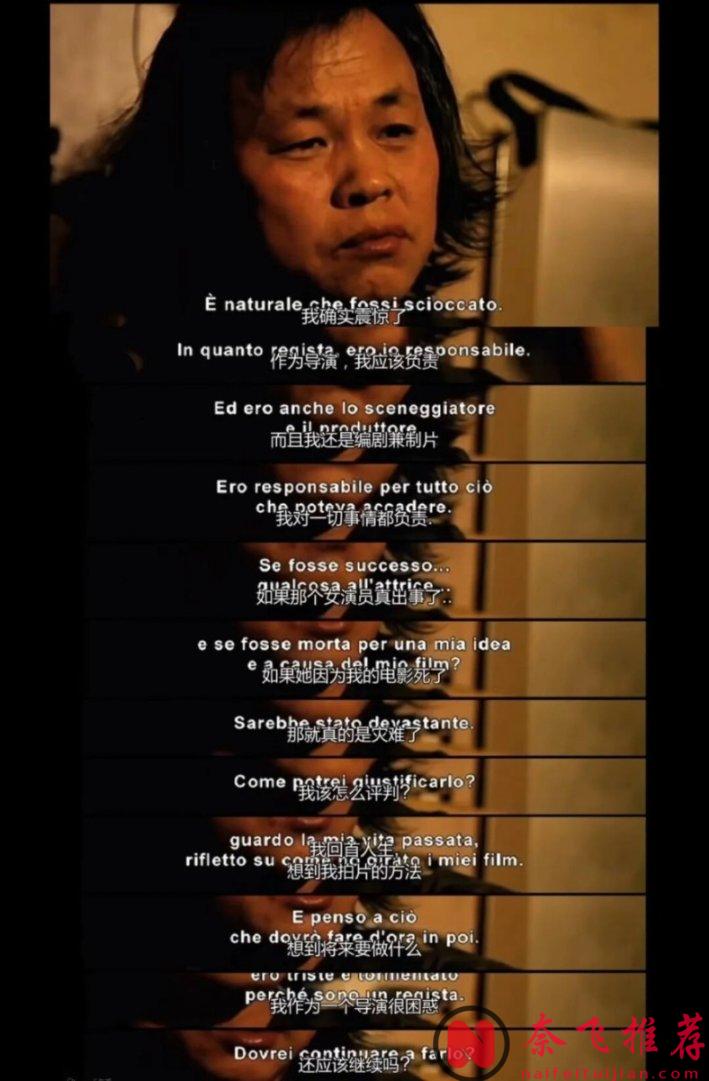
他自問自答,神情複雜。有自嘲,有投入、有哭泣,有麻木,有疑惑,有痛苦,有懷疑......
國人可能根本沒看過他的電影,卻認為他拿了國際大獎是在為國爭光,這讓他覺得很諷刺。
紀錄片的最後,他開車前往不同的地點,分別開了一槍,這大概是他對不同時期自己的處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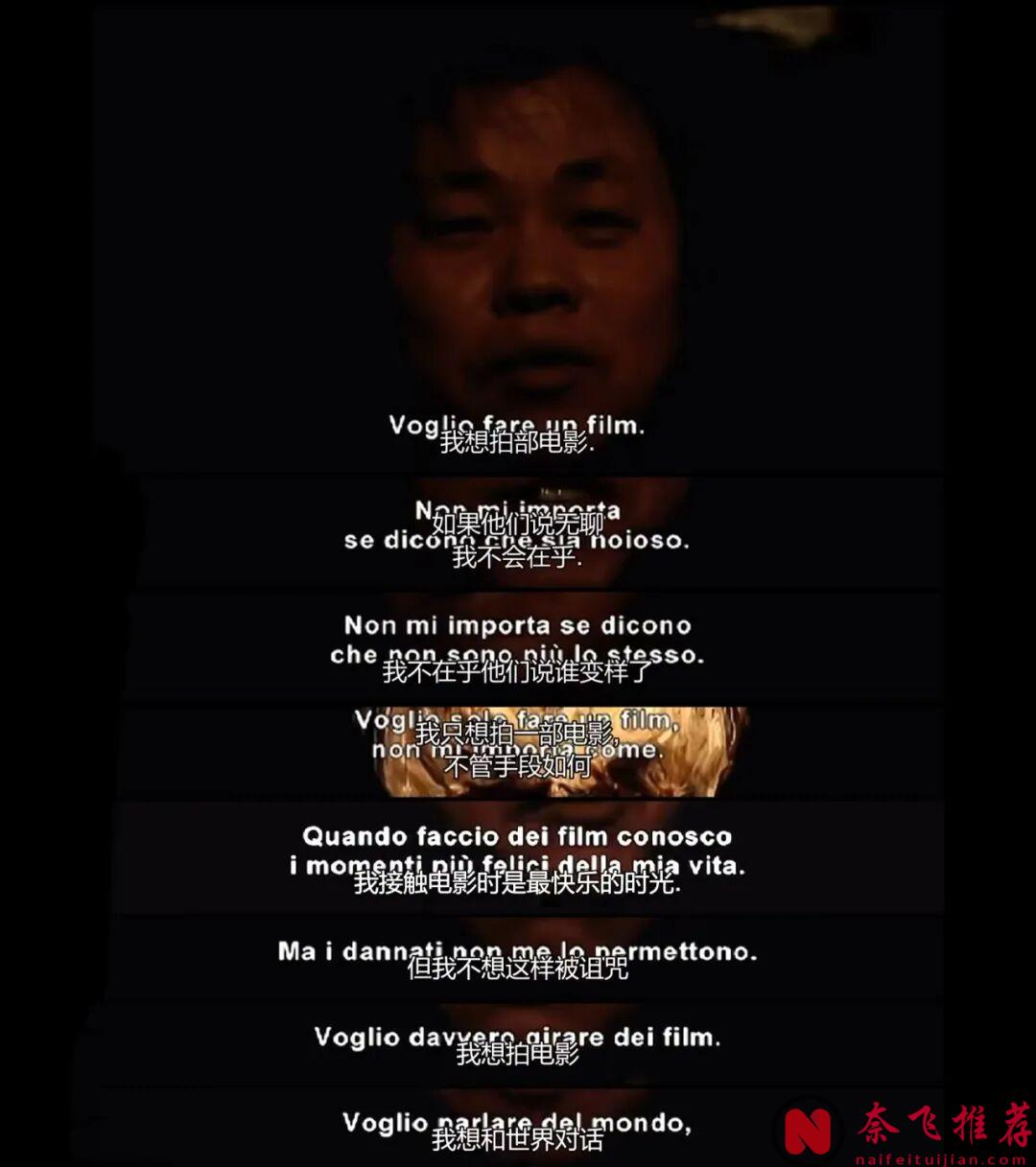
在之後的幾年裡,他接連收到女演員們的暴力指控,扇耳光、語言羞辱、性侵,劣跡斑斑。經過查證之後,金基德獲得了法院的無罪判決。
但他對人性的挖掘和對藝術極致的痴迷,仍舊是建立在對他人的傷害之上,這足以讓他聲名狼藉。

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導演,會像他這樣拍電影。
他的大多數作品,旁白極少,但畫面極具衝擊性,充滿了原始、暴力、血腥、控制、肉慾,極盡生猛。
胃裏翻江倒海,心底一陣惡寒,大腦空白髮蒙,會讓人不自覺地產生一種本能的生理不適,看得人齜牙咧嘴半天透不過氣。但又含各種隱喻,發人深思。

*部分金基德電影
《空房間/感官樂園(港) / 空屋情人(臺) 》充斥著孤獨且浪漫的幻想。
一個遊走於他人空宅的沉默男人,一個常年遭受家暴的中年女人,兩人在無言的默契中相愛,發展出一種超越物理的幽靈般的陪伴。
這部電影沒有對話,只有靜謐空間裡的細微聲響和眼神流轉,在表達一種極致的渴望:絕對孤獨的靈魂,需要更純粹的同頻。


《聖殤/聖母憐子圖 / 母與子》則是另一種關係的極端。
一個十惡不赦的高利貸混混,卻被一箇中年女人聲稱是她走散多年的兒子,他最初暴力拒絕,到逐漸相信,最後深陷親情無法自拔。幾乎都快忘了自己造過的孽。隨著女人的死,這段“母子關係”才漸漸揭開謎底......
這部只花了10天拍攝的電影,卻為金基德攬下了數個國際電影節的大獎,也將他的殘忍美學推向了巔峰。


《時間/慾望的謊容(港) / 謊顏》(也叫《時間的謊容》)則直接地展現了親密關係的脆弱。
患得患失的世喜爲了重塑愛情不惜換臉,變成更美麗的女人接近男友,二人關係的升溫,卻讓女人意識到這纔是更真實的背叛,她在親密中試探,也在親密中迷失......
它一定程度上對映了金基德對愛情本質的不信任。愛情,建立在皮相與感官之上,極易崩塌。

《悲夢》則更玄妙。
李娜英與小田切讓,俊男靚女本應是讓人怦然心動的設定,但金基德卻把它處理成怪奇陰鬱的敘事。
一對男女總是陷入對方的夢境,並在夢中支配著彼此的行為,兩人共生共存,無法入睡,無法掙脫。愛慾與掌控、傷害與依存,一時難以分辨。


金基德的電影,很大程度上也是他自己人生的投射。
他出生在韓國一個貧窮的山村,父親是位退伍軍人,戰爭的創傷使他情緒反覆無常,吃飯時父親的咒罵是金基德從大到大的日常。
中學時,哥哥被學校開除,他也被牽連早早輟學。在極度看重學歷的韓國,他卻只能在工廠、部隊和底層社會間遊走,金基德目睹了太多社會邊緣人的生存法則。
這些粗糲、野蠻的生存經驗,為他早期的電影提供了原始的養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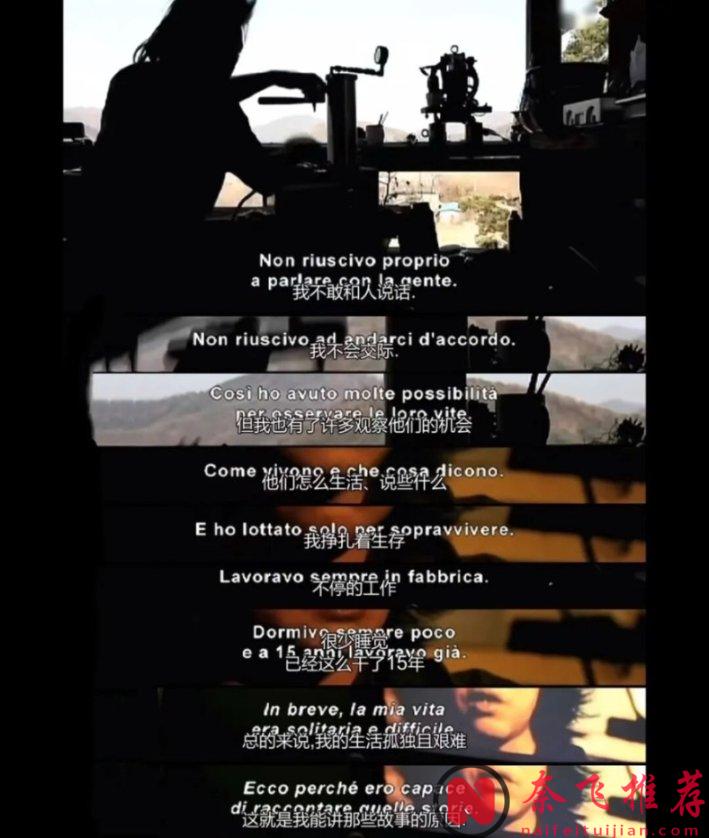
《野獸之都》裡,兩個韓國青年混跡於巴黎街頭,他們被都市的靜默與疏離驅趕到社會邊緣。流竄、掙扎、偷竊、犯罪,那種動物般的求生欲,幾乎是他自身經歷的再現。
三十歲那年,金基德想要學習美術,用全部積蓄買了一張飛往法國的機票,但等待他的,是漫長的流浪之旅。
或許一切早已埋下伏筆,未來某天他將用灰暗的色調、混亂的畫面、暴力的現實,將美麗都市的幻想無情揭穿。

2020年12月,他死在拉脫維亞,死於新冠。
一代天才怪導陡然離世,卻沒有多少討論的聲音。韓國網民表示遺憾但不想悼念。
“我想我如果死了,金基德會被重新提起。那些憎惡我的、否定我的人,在我死後,會以另一種態度爭先恐後地看我的電影。”
他一語成讖,還帶點自命不凡的篤定,他未曾覺得自己對人性和電影痴迷真的有什麼錯,而是世界從未理解他的痛苦。
藝術能穿越道德的審判,直抵人心最複雜的真相。他的電影,就像一面冰冷而誠實的鏡子,倒映他極致的痛苦,也照出我們共有的、幽暗的人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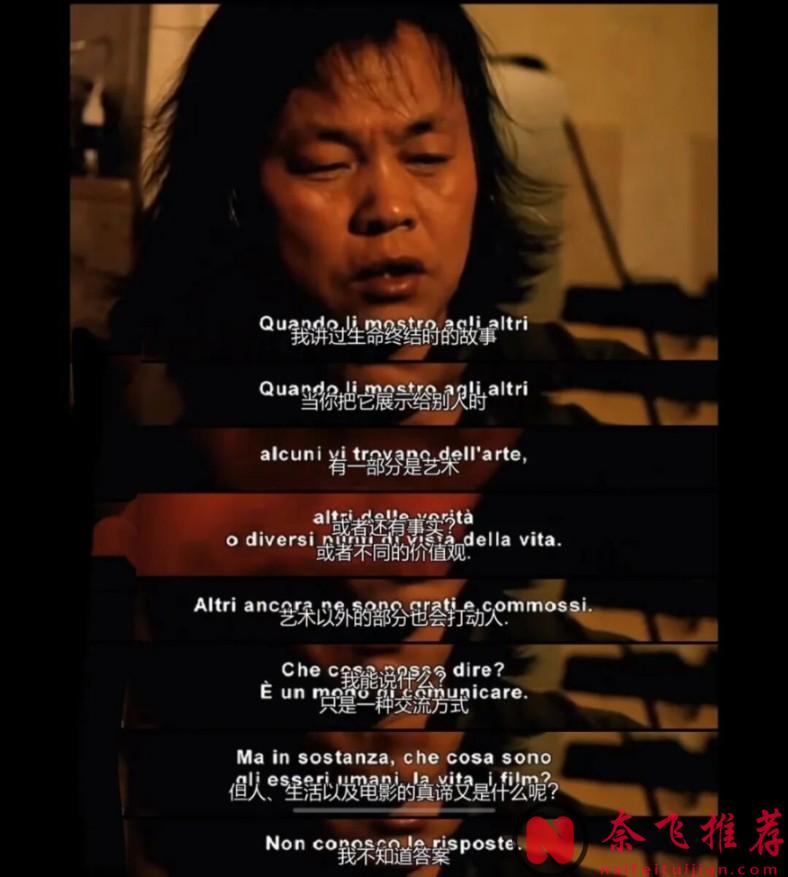
*文中圖片均來源於金基德電影作品
金基德踐行了自己的名言:“人生就是自虐、施虐和受虐”,也承受了一切結果。
他是一個跳脫於正常敘事與主流道德的人,偏執暴虐、臭名昭著,我們不必為他辯駁。但也不必蒙上眼睛,否定他的才華與作品所帶來的戰慄與思考。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