愛看怪物片的小夥伴,肯定不會對墨西哥導演吉爾莫·德爾·託羅陌生。
從《潘神的迷宮》、《環太平洋》、《地獄男爵》到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的《水形物語》,“陀螺導”一直致力於在充滿奇幻色彩的故事中探討嚴肅黑暗的現實主題,在恐怖醜陋的怪物身上描繪純粹的愛與美、神秘與崇高。

在他的作品中,怪物往往同時是人類社會的邊緣者與自然意志的承載者。
就像《水形物語》中不會說話的魚人,被人類捕獲,被軍方研究與折磨,被同爲失語者的女主拯救收留,他莫名捲入到複雜的人類社會中,一路感受著人性裡的殘忍暴虐、愛意溫柔,最終完成理解與審判,又回到自然之中。

“自然就是自然,不存在好與壞,也不需要應對人類的法則與要求。”這便是陀螺導賦予他所造“怪物”的純真。
時隔多年之後,他又推出一部重磅怪物大片。
不過這次不是原創劇本,而是根據已被演繹過無數次的科幻鼻祖改編——《弗蘭肯斯坦》。

《弗蘭肯斯坦》被譽為世上第一部科幻小說,由瑪麗·雪萊創作,最初出版於1818年。
這個故事很多人都已經耳熟能詳了,講的是一個叫維克托·弗蘭肯斯坦的醫生醉心科學實驗,用屍體碎片拼接成一個怪物併成功復活了他。但甦醒的怪物兇殘恐怖,醫生無法控制他,嚇得棄他而逃,最終被怪物殺死。
弗蘭肯斯坦指的是醫生,小說中怪物並沒有名字。不過在小說發表後的幾百年裡,人們漸漸也習慣用這個名稱指代二者,因為醫生的瘋狂行徑也無異於怪物。

原著的故事非常簡短,影片對兩名角色都進行了填充,並採用雙視角敘事,前後兩個章節分別以醫生與怪物各自的視角展開故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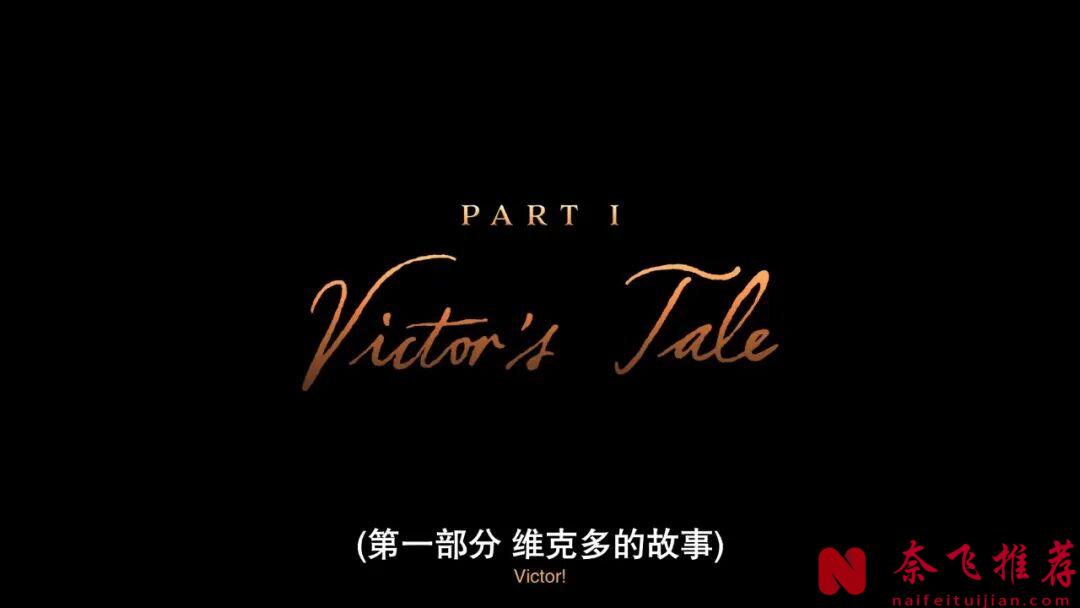
在第一章中,主角維克多·弗蘭肯斯坦出生於一個富裕的家庭,母親是貴族,父親是外科醫生。
他性格陰鬱,童年並不幸福,他的父親是個冷漠、嚴厲而又專制的大家長。
維克多隻能從母親那裏獲得關愛與溫情,但母親在婚姻裡飽受折磨,生下弟弟後便難產而死。

他一度認為,父親當時是故意不救母親的,因為他能看出來,父親看不起他和母親,對他們沒有一點愛。
但當他鼓起勇氣問起時,父親卻坦然道:即便是醫生也無法戰勝死亡。

這句話給了他極大的精神重創,也激起他瘋狂的勝負欲——如果自己能征服死亡,就能向父親投去蔑視的眼神。
當天晚上,他還做了個夢,夢裏自己一直許願的天使應允了他的夢想。
這讓他覺得,自己或許就是能創造奇蹟的人。

從此,維克多沉迷在醫學研究中,一晃多年過去,父親也去世了。
他的弟弟已經準備結婚,他由這重關係認識了一個姓哈蘭德的軍火商。

哈蘭德非常欣賞他,給他提供資金、研究場所,還讓他在死刑犯和陣亡士兵中隨意挑選合格的屍體。
唯一的條件是,未來要滿足哈蘭德一個願望。

於是,男主在一所偏僻的城堡中盡情研究,用無數屍塊拼出一個高大健美的人體,甚至為他製作了比人類更完美的內循環系統。

終於,在一個雷電交加的夜晚,他利用閃電和精心設計的儀器喚醒了這個怪物。
可這時哈蘭德告訴他,自己早已病入膏肓,之所以資助他研究,就是爲了能將這副新的身體據爲己有。
男主無法接受造物被人奪走,拒絕了哈蘭德的要求,兩人扭打之間,哈蘭德墜樓死亡。
而怪物就如同新生的嬰兒,伴隨在男主左右,摸索著身邊陌生的一切。

男主給他取了和自己一樣的名字:維克多。
這也是怪物學會的第一個單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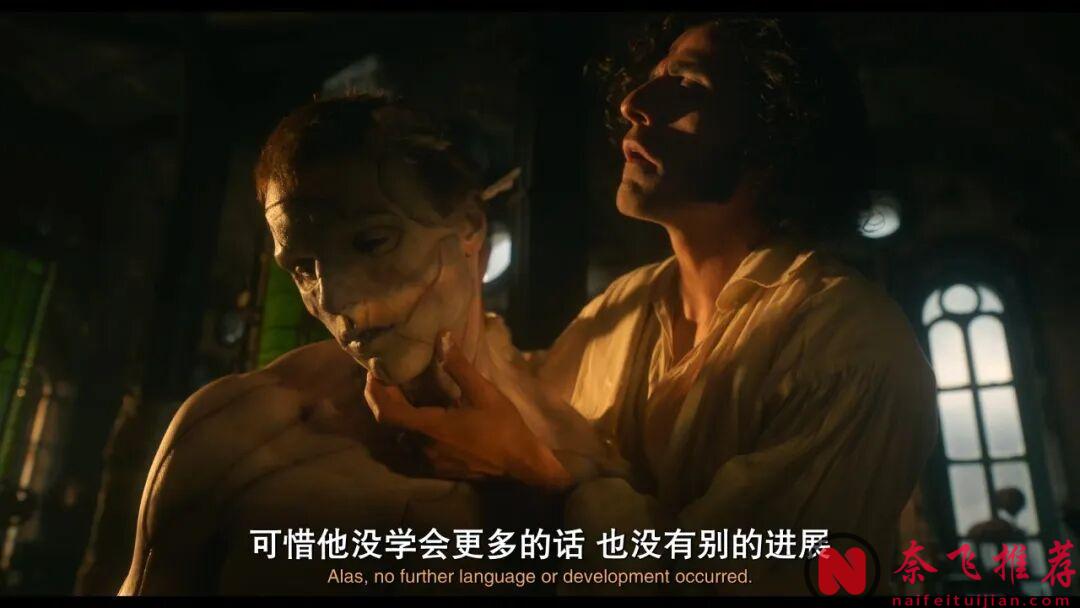
但在最初的驚喜過後,男主漸漸發現,怪物不再有長進,根本無法融入人類社會,而且性格暴力、力大無窮,不論受到什麼外傷都會迅速癒合,沒有辦法控制。

他害怕自己的造物,最終選擇在事態失控前,將怪物和城堡一同炸燬。

當然,這並非故事的結局。
第二章,劇情從怪物的視角展開。

在出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,怪物身邊只有男主相伴,學會的第一個詞是“維克多”,卻並不知道那也是它自己的名字。
它對陽光、水流、樹葉、蟲鼠,見到的一切都感到好奇,會拿起鋒利的手術刀紮在手上,然後看著傷口癒合。

男主害怕它的能力,平時將它鎖在地下室裏,試圖教給它人類的常識。
但它始終沒能學會第二個單詞,看起來毫無交流可能,男主逐漸失去耐心,對它暴力相加。

怪物沒有真正反抗過男主,或許是不明白這一切的意義。
直到男主炸燬城堡,它在廢墟中無聲地痊癒,才真正踏上探索世界的旅程。

它走到森林中,見到樹木,學著林間野鹿吞吃果實,儘管自己並不需要進食。
它給野鹿餵了顆果子,看見這個生靈毫無防備地靠近自己,心裏升騰起一股奇妙的感覺,嘴角上揚了兩毫米。

但下一秒,小鹿就被躲在樹後的獵人擊斃。
怪物被嚇了一跳,隨後悄悄跟著獵人們回了家。
這一家人裡,有個眼盲的老人和年紀尚幼的小女孩。白天大人們出門打獵,只有老人在家拿著畫片教女孩認字,給她講故事。

怪物就這樣躲在附近,接受本該由父母帶來的教育。
有時它會趁夜晚偷偷去林中砍柴,將木材累在小屋門前作為報答,獵人們還以為自己是受到了“森林精靈”的賜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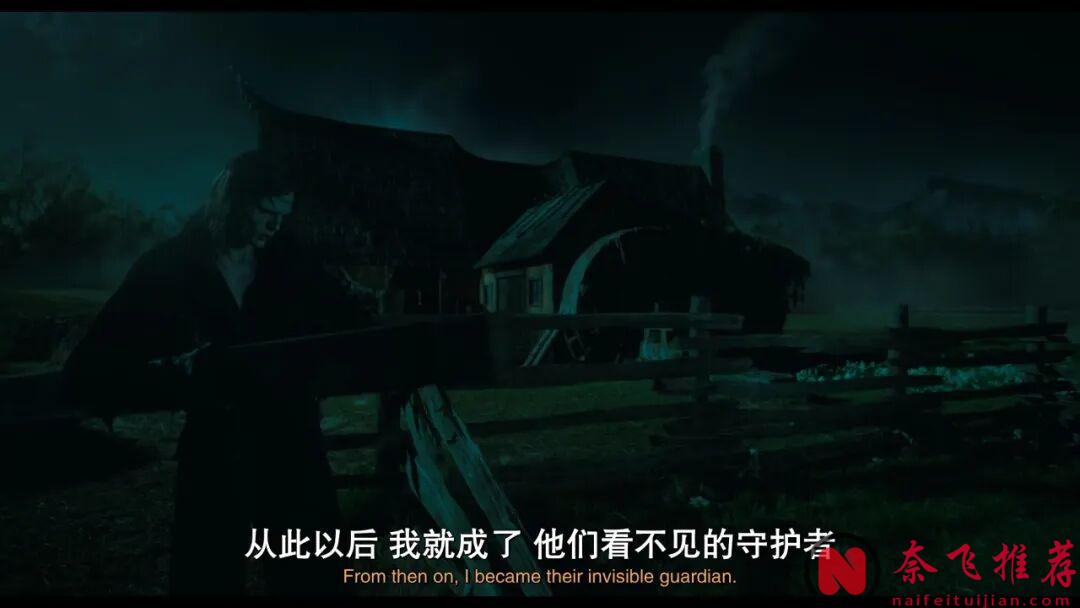
後來,大人們帶著孩子去城市裏生活了,老人自願留下。他早就意識到,一直有一個什麼人躲在家裏。
盲眼的老人和“森林精靈”成爲了朋友。

可惜不久之後,老人也死了。
怪物產生了對陪伴的渴望,它回到曾經的城堡,在廢墟里得知了一切——原來自己不過是一個失敗的實驗品,一個本該被報廢、卻無法真正死亡的怪物。

它歷經艱難找到男主,請求他給自己創造一個同伴。
可男主無法抑制恐懼與厭惡,告訴它就連它本人也不該存在。

然而怪物已經誕生了,它擁有情感、意志,也學會了思考。越是思考,越感到痛苦,因為它所渴求的一切都無法得到,就連死亡也無法做到,只能孤獨地永遠作為怪物在世間遊蕩,這一切都是因為男主的瘋狂與自負。

怪物憎恨自己的造物主,不斷追殺他以復仇。
最終將他殺死,看著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悔悟。

而它自己,只能孤獨地接受永生的命運……

整體來說,這版改編比起恐怖片更像故事片,或者說傳記片。
影片全程並沒有多少恐怖元素,怪物造型也不算可怕,有點像《普羅米修斯》中的“工程師”,不知道是不是致敬了原著小說的全名《弗蘭肯斯坦:現代普羅米修斯的故事》。

相比第一章維克多的自述,第二章中的怪物視角明顯更加有趣,也更能體現陀螺導作品的一貫主旨,透過怪物(他者)的視角審視人類。在這種變換視角的演繹下,同時豐富了原著的內涵。
你可以看到對人性中傲慢與殘忍的批判,爲了享受“造物主”的快感而肆意創造和毀滅自己並不瞭解的生命;

也可以看到對父(母)職的反思,怪物的經歷說白了就是因無法滿足“父親”的期望而被“棄養”,這最終造成了仇恨的反噬;

還可以看到對科技發展的隱憂,比如AI扒取拼湊而成的“創作”,某種角度上也像是一個個賽博“弗蘭肯斯坦”,比如戰勝死亡的嘗試,人類從沒有放棄過,但我們根本無法確信自己的哪步操作,會就此開啟潘多拉魔盒。

或許導演想說的是,不論創作作品還是誕育生命,當我們行駛“創造”的能力時,也要做好準備,承擔隨之而來的後果與責任。





